《哪吒》进入全球票房前10,为何哪吒叙事能引发共鸣?
- 职场
- 2025-02-18 12:54:15
- 16

作者| 萧小壹
媒体人
谁能想到,当天命特权下的灾殃子被魔改成反抗天命的熊孩子后,不仅改变了中国电影市场,还搅动了世界影坛格局:据最新数据显示,《哪吒之魔童闹海》票房已超 120 亿,解锁了超过百项的中国电影纪录,捅破了中国影史票房的天花板,甚至进入全球票房前九。
除去疯狂屠榜的高额票房外,最值得注意的是观影群体的年龄变化:动画电影素来被认为是少年儿童的文化专属,而《哪吒之魔童闹海》直接搅动了 40 岁以上的低频观众,成年观影群体成为票仓的主体。
尽管有着文化亢奋带来的票房增持,但能如此屠戮榜单而又口碑爆表,甚至让低频观众成为票仓主体,在中国影史确乎罕见。如此强大的 " 钞能力 ",也绝非国人自发的 " 百亿补贴 " 运动就能兑现。除去影像制作的精良水准外,文化产品还得靠内容本身说话;尤其是荧幕召唤出来的情感,得真正击中席间观众的柔软之处。
从屠龙少年到屠榜魔童,要从哪吒形象的洗白之旅说起。
被洗白的哪吒:从凶煞、英雄到魔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哪吒。
这位异域神祇进入中国之后,便持续被儒释道乃至民间信仰等文化势力进行本土化改造,逐渐演变成中国文化的神话形象;改革开放后,则根据不同时代的社会情绪进行不同形象的改造,直接以中国神话的荧幕形象呈现给观众。
无论是儒释道文化的本土改造,还是流行文化的影视改编,哪吒都如同莲花重塑肉身那般,不断重获新的生命印记和文化象征:从凶煞、英雄到魔童,从未被定格成型。
据杨斌教授在《全球史的九炷香》中的考证,哪吒形象的早期形象融合了古埃及的重生之莲、古印度的夜叉之神和古中国的儒家孝道等文化元素。随后,再用君权神授的儒家思想将古印度护法神嫁接成了中国将军李靖之子,经由明清小说的魔幻演义而成为天命特权的凶煞之神,同期《西游记》则将之被编入捉拿齐天大圣的天庭秩序护卫队伍。此后,无论是《封神》宇宙,还是《哪吒》叙事,都能看到明清小说的魔幻痕迹。
但如今说起哪吒形象,多数人会追溯到 1979 版《哪吒闹海》:该动画填充了哪吒杀戮的前因后果,用胆小怕事的父亲、无所作为的天庭、丛林法则的社会等衬托出英雄末路的悲壮形象。从此以后,那位在特权护持下仗势欺人的暴戾凶煞,被悲壮正义的抗争形象所取代;反抗父权与反抗权势的独孤形象深入人心,乃至痛仰乐队(全名 " 痛苦的信仰 ")直接以哪吒自刎作为身份标志。
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便不再理会宫崎骏等人所称的政治隐喻,这版经典动画明显镌刻着时代印记,尽管通过配角完善了哪吒暴戾的前因后果,将之塑造成了反抗宗法父权的革命角色,但叙事依旧逃脱不出善恶对立的脸谱化手法,哪吒以外的神魔形象被塑造成了工具版的存在形态。
但也得承认,这版哪吒对凶煞形象的洗白重塑,为近年哪吒形象做了功不可没的先行铺垫。
在饺子导演改编哪吒形象之前,还有 2003 年版央视出品的《哪吒传奇》。这部动漫将历史人物与神话人物交织,建构了一个庞大而丰富的神话宇宙,衬托出哪吒被天选为救世主的正义形象。但是,由于定位给青少年儿童观看,以少年英雄的成长故事作为教化儿童的材料,这部动漫依然因其面向儿童的说教意味,使得观众群体只能囿于青少年之间。

直到饺子导演的剧情改编,哪吒回归人性,英雄归位魔童:哪吒从弑龙救世的末路英雄和天命所选的正义形象再度变成了命定天劫的抗争形象。
饺子版哪吒能够搅动低频观众,在于形象更具象化:从魔丸宿命的出身标签到留守儿童的无聊叛逆,从调皮捣蛋的徒弟到自我觉醒的人子,从天真应试的闯关者到愤怒革命的反抗者,亲情与友情牵绊在身,偏见和枷锁强加于心,人性与魔性共存一体。这一版的哪吒叙事,更贴近真实的人性,更走近大众的情感。
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阴错阳差的魔丸出身,仿佛随机投胎的凡间命数,谁也无法提前左右自身的出身命运,生在何种家庭便注定何等命运。哪吒与敖丙的合体分体,实则如柏拉图所说的生命降世往往携带着一体两面,但无法掩盖的妖怪色彩逃脱不了成长经历的社会偏见。最终在亲情与友情的人性加持下,背负原罪的哪吒在误解与诱骗之后,以莽撞毁灭式暴力美学和颠覆规则的个体觉醒,一举掀翻了规训天下的乾坤秩序。
由此可知,饺子将刻板简化的神话形象进行了丰富的社会化改造,在消解了父权反抗色彩的同时,将宠溺特权加身的哪吒改编为自我觉醒的命运反抗者。
与其说哪吒带有超能力的神魔性能,毋宁说人性被误加魔性,角色的根基终归还是落在熊孩子的人性之上。毕竟,哪吒所反抗的正是魔性所施加的社会标签,而人性才是他真正觉醒的源泉。退一步说,若非亲情友情师徒情等人性情感的濡染,神童也会在社会偏见与规则诱骗下变成魔童。
在神话形象方面,从印度密宗的夜叉神祇到明代小说的反叛神魔,从反抗父权的悲壮英雄到走向世界的人性魔童,哪吒的形象一直在洗白之路从未停滞。而在记忆形象方面,也能看到 1979 年版的末路英雄取代了明清神魔的刻板印象,正在全球热映的魔童形象也将取代上一代记忆中的哪吒形象。
要知道,明清小说中的哪吒形象记忆,也是《西游》《封神》等通俗文学这类流行文化所催生出来的;这一次载入全球影史的哪吒形象,已然宣告了哪怕拥有先前记忆的一代人,也将接受这一版哪吒的崭新形象。

休想挪动的成见:龙族也得翻身,何况申公豹?
值得玩味的是,这部动漫最被观众同情的角色,并不是主角哪吒,而是自我黑化的反派角色。而电影最值得称道的是,配角不再附庸于主角光环,每个人物都被赋予了细节丰富的社会隐喻。
将史诗性神话降维到社会性创作,观众属性也扩散成潜在的社会群体,不再独属于少年儿童,老少妇孺都能从中看到自身命运。饺子建构的魔童宇宙,神话叙事被转换为更加丰富的社会叙事:原生家庭的牵绊,大众认知的偏见,阶层跃升的理想,社会体制的等级,职场文化的异化,等等。
更有甚者,很多人都看到了东方家庭的社会缩影。哪吒也从反抗父权的叛逆先锋变成了为逆天改命而进行社会化搏斗的个体觉醒之人,敖丙从兴风作浪的恶龙形象转变成族群荣耀的升迁工具,龙王敖光也只能在天威强权下屈尊守狱,皆因背负使命而陷入了道德良知与理想抱负之间的两难挣扎境地。
最击中人心的,还得算申公豹家族。如果说龙族算是贵族阶层的话,那么李靖家族则是工薪阶层或公务职员的中产阶层,申公豹家族的草野出身更是映照出了职场打工人的命运缩影。在不公的隐忍与仁慈的不忍之间挣扎的他,替天庭捕杀同类炼丹,希冀获得天庭垂青。一切都是为了摆脱妖族的身份,进而逃脱天庭规则的压迫与社会偏见的歧视,但终归不过无量仙翁的棋子。
投机与仁慈兼备的申公豹,更因家族遭遇而凸显了自身的悲壮:弟弟申小豹尚未修炼成型便前来投奔,战斗力爆棚的父亲申正道在乡野林涧率领妖族勤修苦炼,仅因妖族身份便无从获得世人与天庭的认可,被无量仙翁早早地安排了最终的宿命。最让人动容的是,本可击杀哪吒的他,宁愿自断手臂也不给儿子与族群蒙上污点,甚至劝诫族群接受天庭改造,生怕家族档案将有不为天庭所容的污点履历。

天庭对妖魔的偏见,是威权势力的强制规训,属于权力的宰制;世人对妖魔的成见,是社会文化的无形规训,迎来污名的排斥。在强权规训与社会成见之下,连龙族都要步步惊心,生怕不小心就会遭遇天庭的惩罚而永世不得翻身,其他龙王为了摆脱炼狱则选择合谋,敖闰的 " 我没得选 " 便是偏见宰制下的自我弃绝。所谓龙宫不过天牢,在无量仙翁步步为营的大棋中,差点沦为炼丹炉里的丹泥炉灰。
由此可知,在天庭成见和社会偏见之下,哪怕如龙族参与仙界任务、妖界日夜修炼不害人,哪怕如石矶和土拨鼠般不问世事,就像哪吒展现善心也无从获得认可一样,妖族的身份让他们永世无从获得承认,只能被无量仙翁扔进炼丹炉。唯有升仙才能让族群摆脱炼狱的宿命,但升仙资格早就因身份而被取消。它们徒劳无功地信奉着道貌岸然者的虚假规则,实则不过随机幸存而已。
在第一部中,申公豹说:"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 ";在第二部中,哪吒喊:" 世人的偏见是座山,但我偏要一脚踢碎它!" 当哪吒戳破偏见的谎言,展现觉醒的抗争之后,被强权与偏见压得无法喘气的底层弱势群体也被迫奋起抗争,共同加入逆天改命的现实秩序破坏者队伍。因为前方无路,只能踏出新路才有希望;因为天地不容,唯有扭转乾坤才能自救。
最终,隐忍的父辈们,如信奉天庭秩序的申公豹父亲,在面对天庭无差别的杀戮收网时也喊出 " 快跑 ";再如李靖或龙王,父子之间实现了新的代际磨合,当象征天道秩序的定海神针轰然倒塌后,敖光不再强加使命给敖丙,而是感慨:" 父辈的经验,毕竟是过往,你的路还需要你自己去闯,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吧!"
从个体发出命运觉醒的自我抗争,到父辈说出忠于自我的代际磨合,再反观社会偏见下的卑微异化,当我们看到连顺从服帖的鹿鹤两人都借机狂揍无量仙翁的喜剧彩蛋时,在走出影院吸入户外凉气时,想必谁都能在残余的脑海中回荡着自身的影子。或许,哪怕熬夜狂刷豪门宫斗短剧之人,也能共情于这份偏见重压下底层翻身的社会叙事。
说到底,饺子无非借用了神话的外壳,刻画的却是我们每个人的现实境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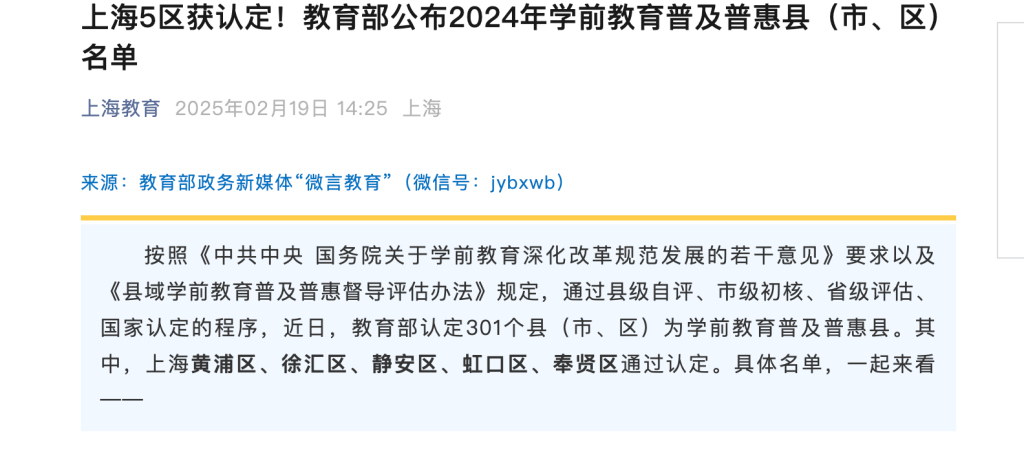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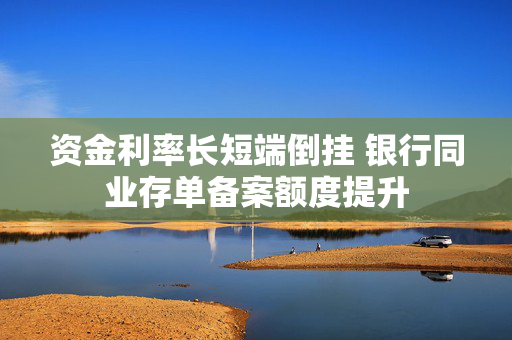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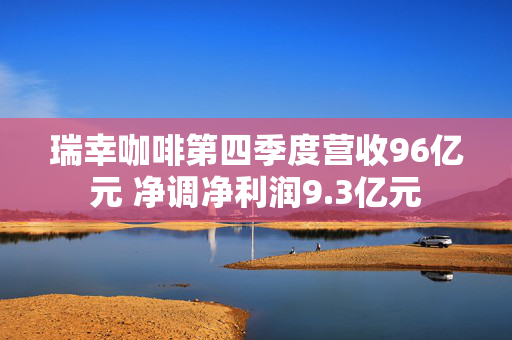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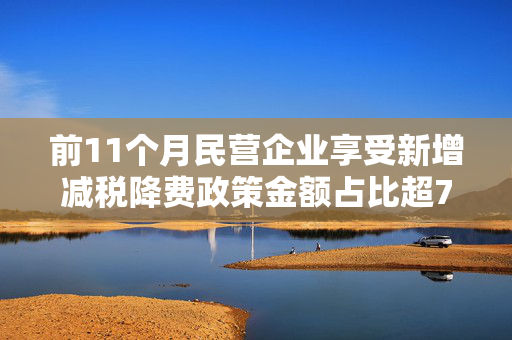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