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峰山的尴尬
- 职场
- 2025-02-19 14:44:26
- 19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顾颉刚与容庚、容肇祖、庄严、孙伏园五人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的名义,前往妙峰山调查进香风俗。5月13日,《京报副刊》特辟的《妙峰山进香专号》开始刊行,顾颉刚前后共为《京报副刊》编辑了六期《妙峰山进香专号》以及若干通信,这些文章和通信后来集为《妙峰山》,由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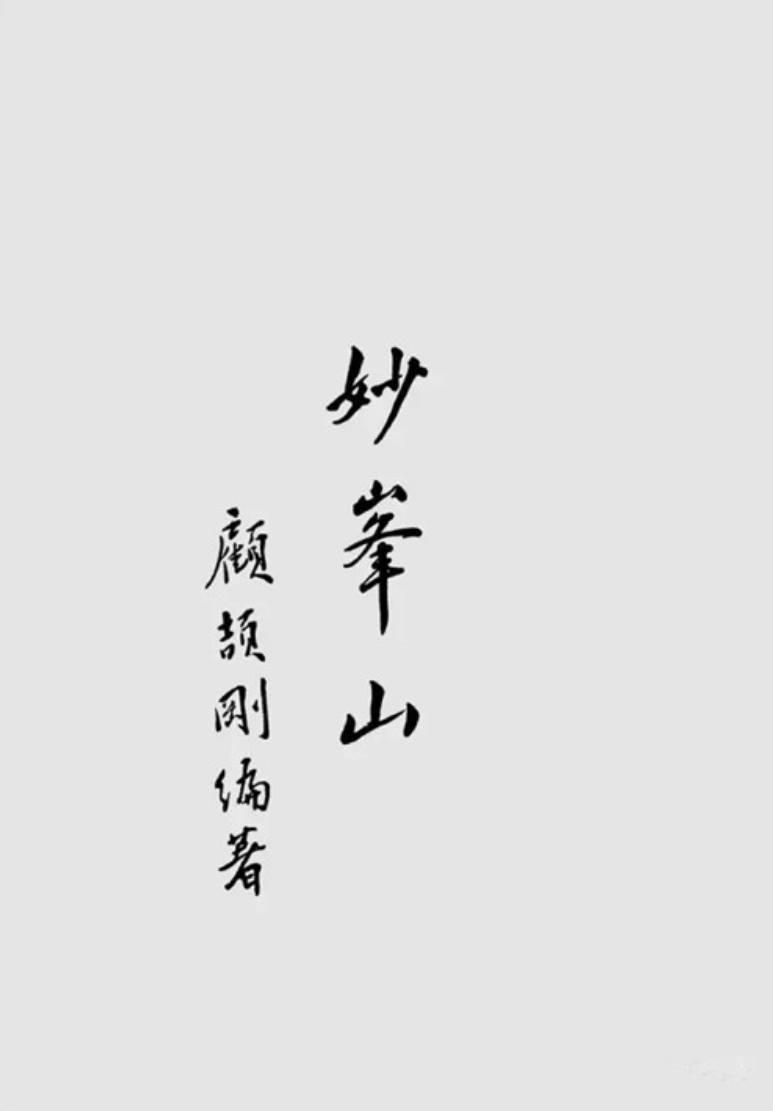
此次妙峰山调查被后世誉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专项田野调查”。就顾颉刚本人而言,他对这次调查也颇寄厚望,这一点从他为《妙峰山进香专号》所写的引言很容易看出。在这篇文章中,针对为什么要进行妙峰山进香调查的提问,顾颉刚从两方面给出了回答:
第一,在社会运动上着想,我们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本来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到了现在,政治的责任竟不由得不给全国人民共同担负,智识阶级已再不能包办了,于是我们不但不应拒绝他们,并且要好好的和他们联络起来。近几年中,“到民间去”的呼声很高,即是为了这个缘故。然而因为智识阶级的自尊自贵的恶习总不容易除掉,所以只听得“到民间去”的呼声,看不见“到民间去”的事实。
我们若是真的要和民众接近,这不是说做就做得到的,一定要先有相互的了解。我们要了解他们,可用种种的方法去调查,去懂得他们的生活法。等到我们把他们的生活法知道得清楚了,能够顺了这个方向而与他们接近,他们才能了解我们得诚意,甘心领受我们的教化,他们才可以不至危疑我们所给予的智识……
妙峰山进香,是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决不是可用迷信二字一笔没杀的。我们在这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意欲的要求,互助的同情,严密的组织,神奇的想像;可以知道这是他们实现理想生活的一条大路。……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件事,有志“到民间去”的人们尤不可不格外留意。
第二,在研究学问上着想,我们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从前的学问的领土何等窄狭,它的对象只限于书本,书本又只以经书为主题,经书又只要三年通一经便为专门之学。现在可不然了,学问的对象便为全世界的事物了!……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因此,我们决不能推崇《史记》中的《封禅书》为高雅而排斥《京报》中的《妙峰山进香专号》为下俗,因为它们的性质相同,很可以作为系统的研究的材料。我们也决不能尊重耶稣圣诞节的圣诞树是文明而讥笑从妙峰山下来的人戴的红花为野蛮,因为它们的性质也相同,很可以作为比较的研究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在此把“在社会运动上着想”的考虑排在了“研究学问”之前。顾颉刚一向给人的印象是严谨的学者,在其写于1926年初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他总结自己是一个没有从事文学和政治活动“才力”的人,从“个性”和“环境”而言,“考证的学问”方为己身正途。但从1925年的这篇《〈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来看,社会运动上的抱负仍是此时顾颉刚从事妙峰山调查的一个重要面向。当然,《〈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观点形成的背景原因可能是多重的。与顾颉刚一起参与了妙峰山调查的孙伏园,不仅是此时《京报副刊》的负责编辑,而且一年之前,孙伏园在自己当时负责的《晨报副刊》上刊载了周作人整理的徐文长主题的民间故事,被主事者叫停,此事成为孙伏园去职《晨报》的导火索。此番孙伏园亲身参与“套了黄布袋去拜菩萨”之事,非议自可想象。顾颉刚从民众运动角度切入妙峰山调查的必要性,大概也有为自己及同人正名,表明调查并非提倡迷信,与同善社、悟善社等同流合污之意。
然而,后续的历史发展却并不如顾颉刚所预料。《妙峰山进香专号》嗣后遭遇的,与其说是反对者的非难,不如说是顾颉刚曾刻意与妙峰山调查相连接的“社会运动”:1925年5月13、23、29日,《妙峰山进香专号》连载三次,5月30日,五卅事件发生,学生运动、群众运动的风潮迅速从上海蔓延到了北京。6月2日,北大学生决议罢课;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各校代表开会,到会学校九十余所,决议即日起北京各校一律罢课。同日,北京学联还组织了游行示威,参加学校百余所,学生五万余人。6月6日,北京各界成立“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雪耻会于6月10日发起北京国民大会,报载参加人数达二十万,会后数万人冒雨游行,行至外交部和执政府递交大会决议案,外交总长沈瑞麟和段祺瑞均与游行群众相见。其后直至9月底、10月初上海反帝大罢工结束,北京持续处于抗议和援助的浪潮激荡之中。
《京报副刊》上首次出现与五卅相关的内容,是北京学生开始集体罢课的6月3日,孙伏园于卷末写了一篇短评。次日又刊登了一篇自上海投递的文章《上海的空前大残杀》。从《京报副刊》的报道情况和言论态度来看,至少在初期,孙伏园及其周边的新文化同人群体对于五卅事件引发的社会运动形势是抱有一定的疏离和疑虑的。孙伏园在6月5日的评论《游行示威以后》中,一方面语带讥讽地指出“打倒帝国主义”这样的口号对于民众水平来说还太过抽象,因而在游行中出现口号愈喊愈走样的状况,另一方面也认为智识阶级在“对于民众的帮助”“对于表率群伦”上都还有欠缺。这种对于民众和智识阶级的双重怀疑,本来就与鲁迅、周作人提倡的“思想革命”以及总体性的国民性批判思路紧密相连。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五卅爆发前,也正是鲁迅、周作人、孙伏园等“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关于女师大风潮问题开始进一步复杂化了。
五卅前后,顾颉刚在这一变动中的新文化阵营内部的位置,是较为中立和模糊的。他一方面是胡适的得意弟子,主张从实际和具体问题着手,强调学术研究对解决社会问题有益,可看出现代评论派主张的影子。但另一方面,他也是早期的《语丝》同人,身兼创办人和十六个“长期撰稿人”之一。具体而言,顾颉刚的民俗学研究和妙峰山调查也可反映出其能同时跟两边接榫的关联点:《语丝》一直把民俗学/民间文学看作思想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江绍原尤为寄望从民俗学研究中发展出一套合乎人性的新“礼”学。在致江绍原的信中,顾颉刚就将妙峰山调查解释为从研究“今礼”到“古礼”的“一个发端”。而顾颉刚在《〈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中论及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于民众运动的重要性,也与现代评论派的“专业”姿态同调。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在五卅发生之前,北京的新文化同人群体的分裂已呈公开态势,顾颉刚的妙峰山调查,至少在诉求上,多少还保留着一种“五四”以来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相融无间的遗风;同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妙峰山进香专号》遭遇的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运动的五卅挑战,以及顾颉刚本人对此做出的反应,就颇耐人寻味。
尽管孙伏园在五卅初期对于事件的反应并不十分热烈,但惨案对北京的青年造成了巨大冲击是毋庸置疑的。从1925年6月8日开始,《京报副刊》的日常刊载基本中断,完全为《上海惨剧特刊》《沪汉后援专刊》《救国特刊》等五卅特刊取代,基本到7月才开始恢复正常刊载。在这些五卅特刊中,《上海惨剧特刊》由清华学生会主撰,《沪汉后援特刊》由北大学生会主撰,《救国特刊》由北大学生组成的救国会主办,其他还有女师大附中学生会主办的《反抗英日强权特刊》、北大学生会主办的《北大学生军号》等零星特刊。虽然鲁迅曾怀疑《京报副刊》的此种特殊安排是孙伏园故意为之,不愿就女师大风潮与《现代评论》继续争论,但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学生组织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以每天一期的密集速度持续推出篇幅长达八页的特刊,至少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北京学生对于五卅事件的极高关注和投入。
1925年6月6日,也即是在《京报副刊》开始完全被五卅特刊占据的前两天,孙伏园编发了第四期《妙峰山进香专号》。尽管半个多月前顾颉刚还曾自信地表示,妙峰山进香专号的一大意义在于襄助社会运动,但在突如其来的、真实的社会运动大潮前,妙峰山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主编孙伏园不得不特意在刊首加了一篇《请读者在百忙中再读我们的妙峰山专号》,申明在如此局势下继续刊发《妙峰山进香专号》的理由。该文开篇如此说:
国家如果是一个健全的,那么,即使是在战争的状态之下,科学家依旧不离开他的实验室,艺术家依旧讴歌,依旧绘画,依旧雕刻,哲学家也依旧忍住了眼前的痛苦,探讨精微奥妙的学理,寻求宇宙人生百年乃至亿万年的大计。
这一对比实际上显示出,至少对孙伏园而言,在实际的民众运动形势前,妙峰山的调查研究已经成了“与国家大事无关而为学术家所不可也不忍忽略的”象牙塔式的工作,而非如顾颉刚所说,为“有志‘到民间去’的人们尤不可不格外留意”之事。
有趣的是,顾颉刚本人倒是很快投入到了五卅的宣传活动之中。6月7日,顾颉刚为上海事作传单二通,经潘家洵(介泉)修改后,由北大同人集资付印二万份,6月12日顾颉刚还亲与潘家洵等人至安定门一带散发。这两份传单同日也由孙伏园刊登在《京报副刊》的《上海惨剧特刊》第五号上。此外,6月9日,顾颉刚还应邀加入了北大学生组成的救国团,此后至10月间一直担任救国团文书股的工作,为《救国特刊》的编辑出版做了大量工作。顾颉刚也撰写了不少与五卅相关的时政文章,大多以“无悔”的笔名发表在《救国特刊》上。
当然,顾颉刚对五卅宣传的热心,除开本人对于政治的兴趣外,也有友人影响的因素存在。顾颉刚友人潘家洵从五卅事件甫始即极为热心,6月3日北京学生大游行,顾颉刚仅在学校观看学生列队出发,潘家洵则随队参加;顾颉刚加入救国团,也是潘家洵代为应允的。此外,顾颉刚此时的女性友人谭慕愚(惕吾),亦是五卅运动中的活跃分子,6月3日北京学生大游行中,谭慕愚在游行队伍中发表演讲,并在北大游行队伍行至东交民巷前迟滞不进时,夺旗率而前行。谭慕愚也是北大救国团文书股的成员,参与了《救国特刊》的编辑和撰稿工作。五卅期间,顾颉刚为《救国特刊》写作的稿件在观点上带有一些国家主义色彩,可能就与谭慕愚有关,据顾颉刚日记,1925年6月间,谭慕愚曾几次赠送《醒狮日报》给顾颉刚阅读。
但顾颉刚在五卅中的表现却并不意味着他彻底转变为一个从事政治运动的活动家。纵观他这一时期的活动,可以发现学术工作和政治宣传这两条线索仍是并行地在发展:在编辑《救国特刊》、撰写慷慨激昂的政治宣传文章的同时,顾颉刚也写作了《〈虞初小说〉回目考释》《金縢篇今译》等古史讨论文字,以及歌谣、孟姜女等民俗学研究篇什。顾颉刚似乎并没有遭遇到需要在政治活动或学术工作当中做出选择的精神困境。但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在1925年7月4日也曾试图写作一篇《妙峰山专号与救国运动》,最终未能完稿。这个小插曲显示出,至少对于顾颉刚本人而言,妙峰山调查与社会运动的关联是真实的;他也希望能够在五卅这样一个现实、具体的社会运动脉络中,整理清楚自己学术工作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原因应该是多重的:顾颉刚本不以抽象思辨能力见长,另一方面,他对五卅的政论态度观点又多来自国家主义者和中国青年党的外来影响,因而在逻辑上,他难于将十分具体的调查方法、资料搜集工作与中国青年党的政论观点疏通融合,也容易想见。此次调和的努力失败后,虽然从顾颉刚的部分政论文字中,仍可看出他运用学术方法来介入政治议题的努力,但基本上直到《救国特刊》结束刊行,顾颉刚的政治宣传与学术研究呈现的仍是平行进行、互不干涉的关系。
1925年10月,《救国特刊》终刊,在事实上终结了顾颉刚的政治宣传工作,但此前谭慕愚与救国团的龃龉,已经使顾颉刚在心理上对实际的政治活动产生了厌倦情绪。1925年8月,谭慕愚因对女师大风潮的态度问题与救国团内部部分成员发生冲突,这最终演变为谭慕愚的国家主义者身份与救国团的国民党派之间的“党争”,并以谭慕愚退出文书股为结果。顾颉刚将此事理解为一腔热忱的谭慕愚因国民党派的派系之见遭受排挤:“救国团以爱国始,而以闹党派意见终,此予之所以不愿参加政党也。热肠如慕愚,终遭罢斥,推之其他事亦可知矣。”
在次年初写作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将包括救国团在内的社会团体的活动认作自身从事学术研究的阻碍,并表示自己缺乏“政治的兴趣”和“社会活动的才能”,只愿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解答“中国民族是否确为衰老,抑尚在少壮?”的问题,以作为他本人“唯一的救国事业”。在顾颉刚的设想中,不文的民众、未接受汉文化的少数民族构成了可能救中国民族于衰老的关键,对民众、地方、风俗等的调查关注因而也成为研究的重点。顾颉刚的研究设计虽然并没有完全脱离他救国、社会改造的理想,但总体而言,此处的民众调查已经不再像他为妙峰山调查所写引言中所述,是一项同时有助于社会运动和学术研究的事业,而完全成了学术研究的分内之事,只是这一研究的成果可能“供给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改造家的参考”。这一变化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五卅对顾颉刚产生的后续影响之一。
顾颉刚在五卅前后的个人经历,以及他主导的妙峰山调查在面对真实的社会运动时的尴尬,部分地折射出诞生于“五四”的、作为一种模式的文化运动,在1920年代中期时所遭遇的困境。这一困境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在“五四”后的进一步深化。五卅事件发生前,北京的新文化群体已经需要面临文化活动的专业化、学院化倾向与作为活生生的“运动”的文化活动、思想革命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争论虽以对女师大风潮的态度差异为表,但其根柢上的不同,则在于如何理解和继续“五四”以来的“文化运动”。此外,“五四”高潮期的社会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推动者、以“新文化”为社会改造的取径,但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等新型政党的成立以及国民党的改组,政党力量的介入不仅分化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青年”群体,而且日益使得社会运动从文化运动中独立出来。
另一方面,五卅运动作为一个真实的社会运动,其极为现实、紧迫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需求,又非谋求以思想革命带动社会实际变化的文化运动在短时间内所能满足的。因而五卅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文化运动模式的危机。顾颉刚1925年前后的经历,从多个层面反映出了文化运动在此时面临的危机和状况:虽然顾颉刚并未介入“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争,其主导的妙峰山调查的设想,无论在方式上还是边界上,都遵循着“五四”创造的文化运动的范式,力图保持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契合无间的关联性。但在现实的社会运动面前,这一调查只能在接受者那里被理解为一种学院的、专业的、与现实无涉的文化活动。甚至对顾颉刚本人而言,虽然妙峰山调查在他的初始设想中与社会运动有紧密联系,但当他面临关联这一调查与五卅运动的反帝爱国、运动群众的具体诉求之时,也只收获了失败。至于救国团的分裂、“党争”与顾颉刚在1926年宣布退守至纯粹学术领域之间的隐秘关联,则更为清楚地呈现了政党政治对社会和文化运动的介入,以及“文化”自身在种种因素作用下朝向专业化、学院化的转型。
如果说顾颉刚的妙峰山调查在1925年的经历,可构成一个从较为外部的角度来观察1920年代中期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关系变化的案例,那么这一案例的缺憾仍在于,它并未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即以文化方式来把握的“民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运动所面临和需求的“民众”存在差异?《妙峰山进香专号》的连载虽因五卅运动的爆发而一度中断,但其在1925年7—8月的后续实际上也并未处理这一问题。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指向了不同的“民众”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京报》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副刊《民众文艺周刊》及其主持者和参与者提出的。
(本文选摘自《地泉涌动:“到民间去”与1920年代中国的文化再造》,袁先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7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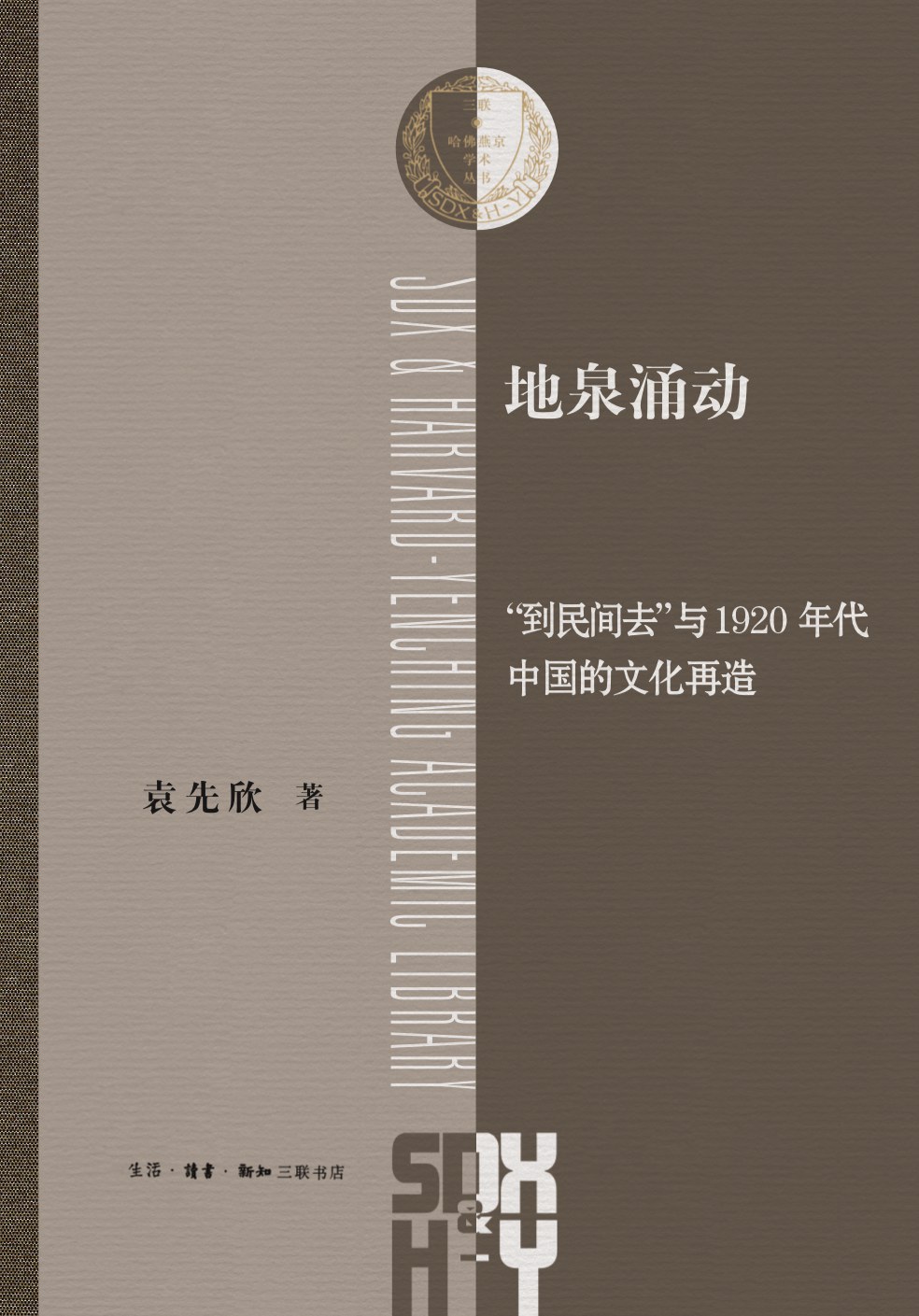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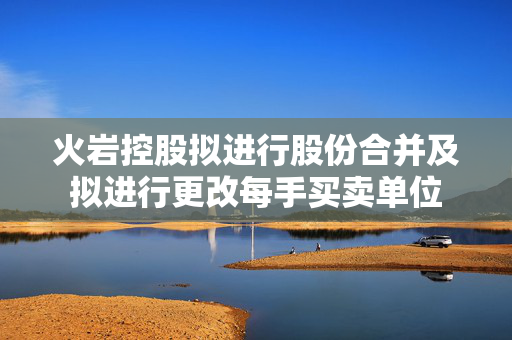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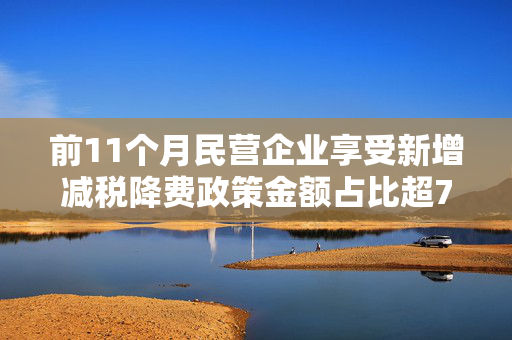







有话要说...